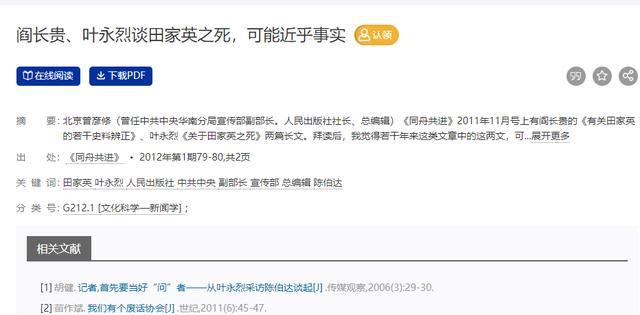1973年成都期货配资,阎长贵在秦城监狱度过了五年多的漫长时光。外界的风云变幻,他已不再知晓。监狱的高墙和那一成不变的水泥地,像一条无法跨越的深沟,将他与曾经的世界隔开。
刚入狱时,他沉浸在绝望与孤独中,几乎没有与人交谈的机会,每一天都像是与自己对抗的煎熬。但就在他快要放弃希望的时刻,监狱的管理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书籍开始进入他的生活,杂志和报纸成了他与外界仅有的联系。即便是这些书籍给予了他短暂的慰藉,可真正的自由,究竟何时才能到来?
投入秦城监狱的日子
1968年1月24日,阎长贵被押入秦城监狱,那一刻,他感到自己彻底脱离了原本的世界。
进入监狱后,他立刻被换上了黑色囚服,代号“6820”成了他的新身份。
这一代号代表了他是1968年第20号政治犯,既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也没有人关心他的过去。

在这座名为“秦城”的监狱里,他彻底成为了一个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囚犯。
每个进入这里的人都会被赋予一个代号,这些代号代替了他们的一切身份信息,几乎没有人再提及过往的生活和故事。这里的一切与外界隔绝,任何外来的联系都被切断。
在监狱里,生活单调得几乎让人无法忍受。
每天三餐的时间固定,除去进食,几乎没有其他活动。即便是和其他囚犯相处,也是寥寥无几,甚至连同监狱里的其他犯人都不会主动交流。
阎长贵渐渐感到自己的孤独,他的眼前只有无尽的灰暗和单调的墙壁,
除了这三餐,其他一切都被剥夺。
没有纸笔,没有书籍,也没有任何能够抒发情感的出口。那些曾经充实的日子,如今都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回忆。他时常想,自己究竟是犯了什么错,才会沦落至此?
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无法摆脱对过去的回想,他每天都在反思,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被迫承受这一切。
每当夜深人静,他总会闭上眼睛,回想自己曾经走过的路,试图在那些片段中找到自己被关押的理由。

他不敢确定自己是否被完全遗忘,是否有一天会被从这个阴暗的地方带走,或者永远留在这里,成为消失在历史中的一粒尘土。
更衣与物品
阎长贵在秦城监狱的生活,经历了他从未想象过的变化。
此前在功德林,阎长贵曾多次向管理层申请过生活用品,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那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比如毛巾、牙刷、牙粉、手纸等,他始终没能享受到。
可一到秦城,监狱为他提供了一些这些他曾经梦寐以求的东西。
更令他感到变化的,是他被换上了黑色囚服,代号“6820”成了他的新身份。在功德林时,他的穿着朴素,几乎没有太多象征身份的东西,而如今,他的每一天都被这套黑色囚服和代号所定义。他曾经穿着的普通衣物和随意的身份,如今都被彻底替代了。

与之前在功德林的9平方米狭小牢房相比,秦城的14平方米的牢房显得宽敞许多。阎长贵站在新牢房里,感受到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空间感。
房间内不仅有洗手池和马桶,还有一些基础的设施,令他倍感宽慰。虽然这些设施不代表真正的自由,但比起过去简陋的环境,秦城的设施给他带来了一丝喘息的空间。他可以在牢房内走动,至少能消磨掉一些时间,避免自己彻底陷入寂静与孤独中。
尽管监禁的生活依然单调,阎长贵在物质条件上感受到了些许的宽松与改善。过去那些每天紧绷的生活,早已变得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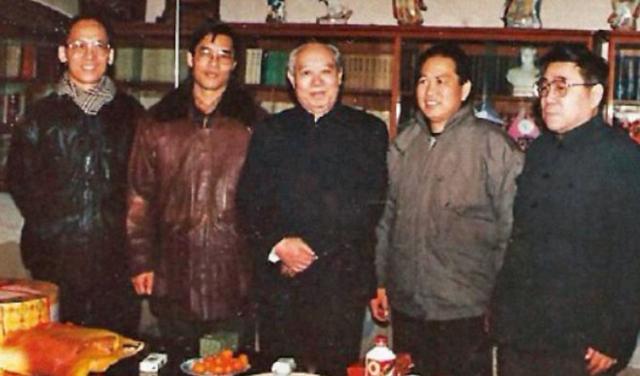
在秦城,至少他可以在这些细微的变化中感到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生活质感。洗手池、马桶这些看似普通的设施,曾经都是他难以奢望的东西,而在这里,它们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生活中的改变
阎长贵在秦城监狱的生活经历了不少变化,尤其是在心态上。最初进入这个地方时,他的内心几乎完全沉浸在孤独与消沉中。他习惯性地将自己与外界隔绝,认为自己被抛弃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他的生活开始变得机械,每天仅仅是在吃饭和躺在床上中度过。时间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他的存在似乎也渐渐模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状态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尽管外面的世界依然与他无关,仍然没有人来审问他,没有人关注他的去向,但他在长时间的孤独中开始悄悄地调整自己,逐渐从那种消沉中走了出来。

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存在,虽然外界的回应微乎其微,但他依然想要做些什么,至少不让自己在这座牢笼里彻底腐化。他决定从身边开始,恢复一点人类最基本的仪式感和生活的秩序。
每天,他都会拿起那块毛巾,开始清洁牢房里的水泥地。他擦拭得非常仔细,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地面上的水泥虽然平平无奇,但在他细心打扫之后,竟然能反射出一点光来。
这种看似简单的行为,逐渐成为了阎长贵在这片封闭世界中的一种坚持。他不再完全让自己陷入消沉,也开始做一些他自己控制的事——比如保持牢房的整洁。
或许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无法决定何时会被审问,无法决定是否能得到释放,但至少他能做一点自己能控制的事。每当看到擦拭过后的地面,他会觉得自己并没有完全丧失对生活的掌控。

与此同时,阎长贵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另一种微妙的变化。他不再完全闭塞自己,尽管监狱里的人们很少交流,他自己也并不主动和别人说话,但他开始偶尔参与到一些简单的集体活动中,或者仅仅是在牢房里走动几圈,做些自己编出来的“囚操”。
这些运动和活动,虽然简单,却在某种程度上让他感到了一丝活力和新的希望。在这座监狱中,尽管他和外界的联系几乎为零,但至少他通过这种方式重新找到了与自己和生活的一点联系。
监狱的放宽
1973年,阎长贵的生活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监狱的管理政策开始放宽,和他过去的日子相比,变化显得尤为显著。最初,这些变化看似微不足道,但对于阎长贵来说,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监狱开始为囚犯们提供《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那样封闭的环境中,这些报刊成为了他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哪怕只是新闻和政治内容,但这也让他感到自己不完全与世隔绝。
除了这些杂志,监狱还允许囚犯借阅书籍,这一政策让阎长贵感到了一线希望。尽管他依然被关押在牢房中,但书籍给了他一个逃离现实的机会。
阎长贵开始接触更多的书籍,这些书籍成为他新的精神寄托。他没有立即选择一些娱乐性的读物,而是决定读一些对他来说更有价值的书。
阎长贵首先拿到的,是《鲁迅全集》。他对鲁迅的作品一直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鲁迅对社会的犀利批判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他仔细阅读每一篇文章,认真品味其中的思想。他把每一篇文章都读得很细,每次读完后,他都会反复思考其中的深意。
除了鲁迅的作品,阎长贵还接触了伟人的著作,其中最让他痴迷的是《论持久战》。这本书阎长贵读了无数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读它时那样认真。
他认真研究其中的军事战略和革命思想,从中寻找出对当下情境的启示。尽管他身处监狱,身心受限,但在书籍的世界里,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一块乐土。
流放到洞庭湖的农场
1975年,阎长贵从秦城监狱走出,他并没有马上迎来自由,而是被流放到了湖南洞庭湖的一处农场,继续接受劳动改造。

与秦城的封闭和严苛不同,洞庭湖的农场给了阎长贵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依然充满了艰难与挑战。农场的生活条件并不优越,环境较为恶劣,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和湿气沉沉的湖泊。
阎长贵的真实身份在这里几乎无人知晓。农场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多少人关心他曾经的过去,而他也并没有过多提及自己的经历。
初到农场,他的工作并没有特殊待遇,和其他劳动者一样,他开始从事一些基本的生产劳动。喂猪、放牛、整田插秧、种菜和煮饭成了他每天的主要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阎长贵的表现得到了农场领导的认可。他开始承担一些更加重要的工作,逐渐从简单的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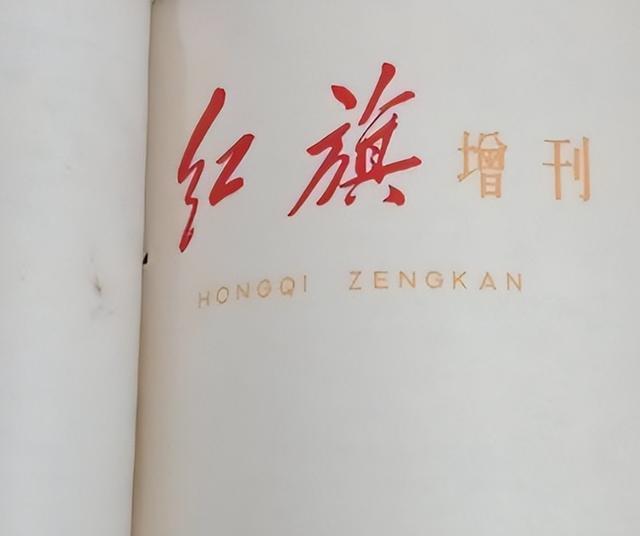
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改造,农场开始将他调入农场中学,担任教师一职。在这里,阎长贵不仅开始教授一些基础的文化知识,还承担了教导农场孩子们的责任。
此后,阎长贵的地位逐渐提升。他被抽调到农场的宣传部,担任了理论干部的职务。这一职位让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和参与一些农场管理和理论研究的工作。
他开始承担更多的责任,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劳动者,而是参与到农场的文化建设和思想宣传工作中。

直到1979年9月,经过了长达12年的牢狱生涯,阎长贵终于迎来了平反。他从农场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还正式恢复了自己的名誉和身份。1980年3月,阎长贵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曾经的工作岗位——《求是》杂志社。
参考资料:[1]阎长贵、叶永烈谈田家英之死,可能近乎事实[J].同舟共进,2012(1):79-80